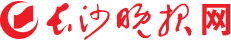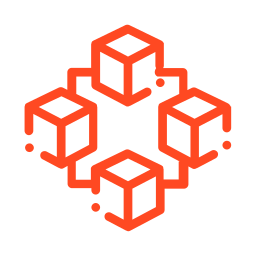银杏黄了
欧阳稳江
“爷爷走了,还会回来吗?”8岁的儿子问后便不再吭声——儿子念着的爷爷,那个偷偷给他买棒棒糖吃的爷爷,那个喜欢和他嬉闹的爷爷这次是真的走了,再也回不来了。
我的思绪飘忽如河底的水草,光线从水面上渗下来,穿透幽深。而站在河岸上的人,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那条名为时间的河。阳光如火焰一样明亮,让人忍不住怀想那些细碎的瞬间……
因为热爱文字,和公公一家结缘亦是巧合。成为家人后,公公在家时多半是严肃的,唯独和老同学老朋友相处时会高谈阔论,以及在逗弄孩子时会有难得一见的松弛。彼时,我将这种飞逝的、主观的印象理解成理科生的底色。或许,像拍照一样,那些不能被预期的瞬间,才是意味深长的。
三年前,公公读高中时的母校举行校庆征文。作为最早的毕业生之一,公公参加征文的热情比其他人都高。几乎一气呵成,将一个贫困少年发愤求学的珍贵履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。文字朴素动人,少年家境的窘迫与师生雪中送炭式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文末,写到爱生如子的校长却在时代洪流中离去,让人唏嘘更让人为之落泪……
这篇回忆真实而可贵,或许在他心中,这段人生记忆不仅仅是进入暮年后内心感情的反复咀嚼和巨大冲击,更是留住属于他和高中母校芳华岁月的唯一途径。原本,公公希望我能作为第一读者提一点意见——读后良久,我除了将篇幅稍作压缩,并将文章标题修改为“芳华”二字外,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修饰。
汩汩而出的文字里,松弛、自由、丰盛的精神世界,大概是公公一生的梦想。这次陡然对他人内心的窥视,亦让我不再执著于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明亮的底色。
接下来的三年,公公的身体一直比较孱弱。最初因为喉疾,他动了一次大手术,健康急转直下。幸好有婆婆细心照料,他的生活亦算过得平静。由于声带的损伤,让平日里喜欢说话的他极其不习惯。亲友相聚,甚是热闹,他却只能干听着而无法加入,替代的,多是沉默的眼神,让人见了多少有些不落忍。
一年之后,公公突然咳嗽严重。激荡与嘈杂的医院里,会诊的专家们平静地告知了最坏的结果。尽管已有心理准备,但诊断书上短短的几行字依旧让人恍惚。努力平复心情后,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聚集在幽暗的楼梯间一再彩排,只为将善意的谎言尽量说得圆满一些……我知道,对于事事要强的公公来说,他是不会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。
从暮春到深秋,我们天天跑医院。离医院不远的行道上,银杏树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:先是枝头那可爱的嫩绿,点缀在每一根枝条上。日暖风和,树变得越来越丰腴,披上了一层绿烟似的轻纱,坦然地舒展开来;随后,便是绿荫如泻、亭亭如盖,摇着一树的光影,仿佛在蓄积一场静默而盛大的心事。
和银杏树的欣欣向荣不一样,公公所住的病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随着病情的加剧,来回地转科室就诊让他身心疲惫。因为坚信自己没事,最初他每天都会围着医院的大楼散步,直到微信运动的步数达标。慢慢地,散步地点缩小成了病房的走廊。人来人往中,只见一个清瘦的背影艰难晃动,倔强地像是在证明什么似的。到了夏末,公公躯体的力量逐渐丧失,只好改坐轮椅,由家人推到室外透透气,此时的他或许意识到了病情的危重,“努力活”成了全部信念……再后来,我每日的探望,所聊多是琐事,关于健康的话题反而是有些避重就轻。这个话题不像行道上的树木,有着明确的枝干与方向。我们彼此剩下的,惟有“心知肚明”了。
风和日暖的春天过去了,茂盛的夏天也悄悄过去了。夏日里那场浓得化不开的绿,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泄密,让人免不了伤怀。
眼看深秋了,我特意请了年假去医院全程陪护公公。这个时候,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某种预告,病魔带来的疼痛让他完全无法安睡,止痛药的作用微乎其微。不能自主大小便,让他很是不好意思,换洗之时他会幽幽地表示抱歉:“没法控制自己了……”我五味杂陈,只能安慰他,将我这个儿媳当作普通的护工。待收拾妥帖之后,他疲惫地说:“好辛苦!”那口吻,既像是对亲人说的,更像是对自己说的。
往后,关于死亡的话题亦不再是避讳,他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交代,人若去了,服饰应该穿的颜色和式样,以及葬礼的安排。尽管不希望,可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当公公的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时,我看见窗外阳光灿烂,银杏树叶金黄金黄。或许,树叶变换的过程并非衰败,而是一种抵达。
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,思绪如水草,在这深深的、无法可见的水底,压根就感受不到人间的悲欢离合。生命的谢幕,一如秋叶之沉静与通透,唯有在季节的轮回里凋零飘落,才是真切的常态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