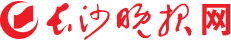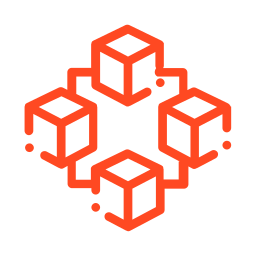行年猪
彭祖耀
过了腊月十五,父亲戴着眼镜翻黄历,择期行年猪,要避开六的日子,因为“六”是“六畜”的吉日,谁都不忍心这个时间杀猪。
行年猪的那天,天麻麻亮,我们便早早起身。推开门,村庄仿佛被一层银霜包裹着,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几只山雀在门前老梨树上喳喳欢叫。
我往灶膛塞进树蔸,以红松针引燃,火苗“噼啪”欢唱,不多时两大锅水便开始翻滚。妈妈在厨房如陀螺般转个不停,碗筷、蒸笼、饭甑在她手中飞速掠过,动作娴熟利落,饭菜的香气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父亲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杀猪用具,扶梯、门板、花箩、木盆一一摆放妥当。
天刚破晓,村里还蒙着层淡淡的晨雾。屠宰匠哼着《打铜锣》花鼓小调,一根长长的铁挺棍挑着个竹腰子篮,里面装着杀猪刀具。他老远就扯着嗓子吆喝:“恭喜哟,恭喜!”
左邻右舍闻声,纷纷撂下手里的活计,从各家涌出。男人们个个摩拳擦掌,撸起袖子,簇拥着父亲进了猪圈。花猪太肥出不了猪圈,喜哥和孟叔一人拽着一只猪耳,一时间,吆喝声、猪叫声,在山冲里回荡。大花猪沉沉地“睡”了。
屠宰匠熟练地在猪的左后蹄切开一道口子,顺势将铁挺棍顺着猪筋的缝隙径直捅向猪头,旋即迅速抽出。紧接着,他深吸一口气,鼓起腮帮子,对准那道口用力吹气。眨眼之间,原本瘫软的花猪如同气球一般,缓缓鼓胀起来,变得圆滚滚的。
紧接着,滚烫的开水浇下,猪毛泡软,众人手持刮刀利落地刮毛。不多时,花猪变得白白净净。随后,用铁钩将猪挂在扶梯上,开边子、割肉、剔骨头。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
男人们在地坪里忙着杀猪的活儿,女人们也没闲着,有人熟练地切菜配菜,“咚咚”的切菜声,仿佛是奏响的过年的序曲;有人烧火添柴,灶膛里的火苗欢快跳跃,映红了迎新年的喜悦。女人们一边唠着家常,一边手脚麻利地准备碗筷,笑声在空气中回荡。
一碗茶功夫,厨房里香气四溢,一道道热气腾腾的杀猪菜陆续上桌。堂屋里六张大方桌摆满了丰盛的菜肴,大家热热闹闹围坐,挤挤挨挨,酒杯碰撞间,欢声笑语四溢。孩子们如欢快的小鹿,在桌间嬉笑追逐,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洒落。亲戚邻里分享着生活的趣事,夸赞着猪肉的美味。此时,温馨与和睦如同冬日暖阳,年味渐浓,杀猪饭成为一年中最温暖的团聚记忆。
饭后,宰猪匠、亲戚和邻居们便各自回家,忙着筹备过年。母亲则开始精心料理猪血,在家乡,这猪血被亲切地称作“猪旺子”,寓意日子红红火火、家道兴旺。母亲带着我和姐姐,端着一碗碗精心做好的猪旺子,挨家挨户地送去。
每到一户邻居家,大家都笑意盈盈地迎上来。吴阿婆眼睛笑成了两条弯弯的月牙:“哎呀,这猪旺子烫得真好,像红绸子一样!你家今年旺,来年更旺!”。一碗碗猪旺子,传递着浓浓的邻里情,也让年味愈发醇厚。
晚饭后,一家人惬意地围坐在火塘边。我吃得肚子溜圆,时不时打出响亮的饱嗝。母亲说她要煎猪油,吩咐我和姐姐去送块肉给村里的憨子爷爷过年。
我皱了皱眉,嘟囔着:“这么晚了……”母亲轻轻拍了下我的手,语重心长:“孩子,今年青黄不接那会,咱家揭不开锅,憨子爷爷虽不宽裕,还送了一勺豌豆救急。咱做人,不能忘恩。”
我和姐姐对视一眼,点点头,提起肉,打着火把踏入夜色。寒风一吹,火苗忽闪,远处山峦只剩模糊轮廓。
回家时,打霜了,可我一点儿也不冷。
姐姐一脸神秘,凑近我说: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明天邻居喜哥哥家行年猪,请了我们全家去吃杀猪饭呢。”
我兴奋得一下子举起火把,大声欢呼:“行年猪啰,行年猪啰……”
火花如星子迸溅,我的欢叫声在宁静的村子里回荡。远处传来“汪汪”的狗吠声,像是在回应这份喜悦。几家农舍的窗户透出扑闪扑闪的光亮,在霜夜里晕出暖意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