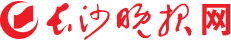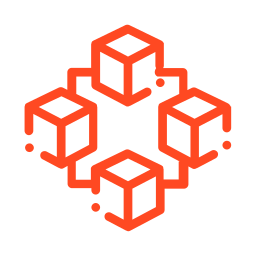散文 | 再续鹦鹉情缘
文 | 朱鹏飞
七年前,一岁多的小女儿对小动物特好奇。我们来到万家丽路和时代阳光大道相交叉处的花鸟市场。店长说人工繁育的虎皮鹦鹉命最贱,容易养。我们挑了对虎皮鹦鹉,一蓝一绿、一公一母。
我住顶楼,楼顶天台基本是我家使用。电梯塔楼有个很长的屋檐。鸟笼挂屋檐下,避日遮雨,得天独厚的养鸟场所。
鸟儿清晨叽叽大叫,好像在宣示主权;心情舒畅时,轻声鸣叫;焦急、饥饿状态时喳喳叫,提醒我该添食了;受惊吓时便呱呱乱叫,伴随撞笼乱飞,甚至飞射一抛绿屎。
鹦鹉进食飞溅出粟米,引来麻雀。麻雀在笼外飞上飞下,笼中鹦鹉很生气,发出嘎嘎嘎尖叫,厉声警告:“我的地盘我作主。不许吃我食物,主人快抓小偷……”要不是被关笼里,估计它们早和麻雀拼命了。近鸟知鸟音,我快成了鸟语专家。
春暖花开时,我把鸟笼摆地上。鹦鹉咕噜咕噜的声音,酷似细语呢喃的两口子,估计到了恋爱季,欣欣然跳跃、和气喧哗。牙牙学语的女儿搬个小凳子围着鸟笼转,活像三个小顽童,各抒己见,鸡同鸭讲,扯上个把小时。
我常瞪着鹦鹉。蓝色母鸟胆小怕事,一有风吹草动就钻进鸟笼中的木箱里。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,从木箱洞口探出头来,警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绿色公鸟好奇心强,不怕人,每次瞪着小圆眼回看我。手痒时,我用小木棍伸进去拨弄绿色鹦鹉,木棍顶着,它才极不情愿地后挪。
晚上,鹦鹉双爪吊在笼子铁丝上睡觉。它们早起早睡,有规律,天刚黑便犯困,两眼半睁半闭。有天晚上,我去看,公鸟突然来了精神,瞪着我。突然,张开勾状的嘴巴打个长长呵欠,估计在骂我吵醒了它。顽皮时,我用手指扳开吊在铁丝上的爪子,鹦鹉乱飞一通后落在栖木上。
我在网上淘鸟食,鹦鹉两三天能吃完一罐带壳粟米。偶尔加入点蛋壳,或者扯一片青菜让它们啄食。
每天起床后,我便往顶楼跑,添水加食成为我的生活,风雨无阻。鸟儿似乎成了家庭成员,即便加班,晚上到家我也是先去看看鹦鹉。前年春节,疫情期间假期拉长,幸好我把鹦鹉带回老家,逃过鸟儿被饿死这一劫。有些爱相遇了,就羁绊纠结,像颗长在心里的种子,心在,不会枯萎。
天有不测风云。去年三月,一天早上添食后忘关笼门,绿色鹦鹉远走高飞了。留下蓝色鹦鹉,我靠近,它习惯地躲进木箱,可怜巴巴地瞄我。其后,它再也快乐不起来,成天在栖木上蔫蔫地耷拉着脑袋,落寞。它苦楚:有爱才是家,老公走了,家没了。它郁郁寡欢,鸣叫声愈来愈稀少,遇到惊吓才尖锐地短叫一句。我怀疑它得了抑郁症。
五月份,我来到花鸟市场。突然萌发奇怪的念头,现今的鹦鹉和我家那只已相隔几个代沟了。我买只文鸟来陪伴鹦鹉,或许活蹦乱跳的文鸟能治愈它的抑郁症。
鹦鹉在弱小的文鸟面前算庞然大物。可文鸟身手敏捷,一进笼子就占领木箱。鸠占鹊巢,胆小鹦鹉竟不敢飞进去,到处乱蹿。不过,一星期下来它们相安无事了。
秋天到来后,我发现蓝色鹦鹉精力大大减弱。它羽毛蓬松着,眼神涣散、行动滞缓,走着走着竟然睡着了,活像耄耋老者。它好不容易来到笼里面的食槽外边,一边脸贴着食槽,头慢慢地下坠,突然一下惊醒。它拼尽全力爬进食槽,又埋头睡在食槽里。晚上,它钻进木箱里过夜,以前冰雪天气都是用爪子钩着铁丝睡觉。
文鸟依旧高声歌唱,上下跳跃。鹦鹉每况愈下,如秋叶飘零、风烛残年。垂暮之年,即将逝去,它已气若游丝,无法逆转的自然规律。
蓝色鹦鹉终于死在秋冬交替的季节。岁月带走欣欣然跳跃的鹦鹉,带走了高高喧哗的声音。我上网查了虎皮鹦鹉寿命为七年左右,算“寿终正寝”。陪伴七年,留给我太多独一无二的回忆,影响着我喜怒哀乐。融入到生命里的东西,失去后,难以释怀。
早一向,笼门未关好,文鸟也飞跑了。文鸟长相漂亮、叫声悦耳,但难互动。养了快一年,见到我,仍当我是陌生人,一靠近,就在笼里乱扑腾。撸猫撸狗撸鸟图个互动,可能是我还没到培养文鸟人情味的段位。
平衡被打破,望着空空如也的鸟笼,老感觉丢了件东西。今年春风又来了,窗外偶尔几声鸟鸣掠过。我又来到花鸟市场,店长不再是那个店长,话还是那句话:人工繁育的虎皮鹦鹉命最贱,容易养。我挑一对虎皮,续上情缘,鸟儿还是那么喧嚣。鹦鹉的喧嚣竟然带给我心灵的宁静。
>>我要举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