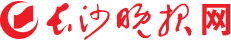乡土传奇的苦难与诗意 ——评长篇小说《南荒记》

■刘智跃
刘鸿伏的《南荒记》是一部内容非常奇特的长篇小说。一幅幅色彩浓烈的风景画,一帧帧情调浓郁的风俗图,给读者独特丰富的审美感受。作为同时代人,我对作家描绘的生活场景感同身受,饥饿、苦难、求学、生产劳动……处处烙刻着时代的印记。这是一种既亲切又新奇的阅读体验。在当下文学追求可读性、通俗化的大潮中,它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比较清新独特的新乡土小说。
《南荒记》小说描述了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。跟外界的联系就靠一条毛板船,与县城有一百多里水路。村里没有电灯,没有汽车。这里的人,靠山吃饭,种地为生,出门爬坡,吃红薯饭,喝竹笕水,住茅棚屋。因其偏僻与闭塞,这里几乎不为外人知道,增添了特别的情调。
与风景的原始奇异之美相比,小说大量渲染、铺排的地方风俗更加奇特。这是一个有神的世界。人们普遍相信万物有生命,有灵性。村中那棵老樟树是成了精的,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穿白衣裤的女人坐在树杈上梳头。打鱼的祭祀河神、水鬼,打猎的祭祀猎神。旱季,人们抬着龙王菩萨求雨。各种日常生活细节充满地方特色,喝酒的名目前所未闻,如猪饮、树饮和龟饮。民间活动如风雨桥上听月琴、大田里舞狮子。丧事活动如吃老饭、洗沐、穿寿衣寿裤、守灵、哭丧、出殡、路祭、下葬等。还有怪异的诈尸、神秘的赶尸、身份特殊的穿衣人……无不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风景描写和风俗展示,像一颗颗洒落的珍珠,缀满全篇,使得小说异香馥郁,满篇生辉,成为小说审美内容一个很大的看点。
新文学乡土小说自鲁迅发端,在百年迁延流变过程中,主要有两大传统:一个是鲁迅开创的启蒙主义传统,还有一个是沈从文开创的文化守成主义传统。从五四乡土小说作家许钦文、王鲁彦、台静农、蹇先艾、彭家煌、许杰等,到20世纪30年代叶紫、吴组缃、沙汀、艾芜、路翎等,一直到新时期作家高晓声、何士光等,都继承了鲁迅的乡土小说写作观念和艺术传统。启蒙主义乡土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文笔描述乡村农民的生活与命运,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。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则别开一面,用主观抒情的浪漫笔调,开启了乡土小说的“田园诗画”风格,是散文化、诗化的乡土小说。这一传统自上世纪30年代废名、沈从文等京派小说奠基,经萧红、孙犁、汪曾祺、刘绍棠等众多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得到继承与延续,并形成了多种变体。无疑,《南荒记》继承并光大了乡土小说“田园诗画”风格。
《南荒记》虽然不像《芙蓉镇》那样,有“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”的政治冲动,但小说还是昭示着比较具体的时代背景。“现在村子里流行着一种叫水肿的病”,再加上“生产队”“知青下放”“破四旧”等信息,时间基本上就比较明确了。小说共十六章,从头至尾铺满饥饿的底色,布满死亡的阴影。残酷的现实、苦难的生活对人是一种磨砺,更多的是一种伤害。这就导致了小说主题和情感上的矛盾。一边是小说诗意叙写的风景与风俗,一边是作家沉重感叹的饥饿与死亡。
《南荒记》这种多视角交织的写法,融入了某种程度的后现代写作特征。小说已经褪去了五四乡土小说的文化启蒙色彩,它对乡村的主观抒情,也不再被看作是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反动。它追求乡村和都市形态共处、文化共生的和谐关系。后现代人的最大悲哀在于,他们既厌倦了现实生活的都市,又无法回到理想境界的乡村,精神无依靠。而摆脱这种状态的最理想的方式,也许就是可以随意寄托精神和栖息身体的大地。
>>我要举报